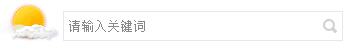参加过叙利亚战争的以色列坦克指挥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程指挥官。他们执行力最强,而且一切以细节为导向。这是建立在20年的实战经验基础之上的—兢兢业业,敏于观察。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1973年10月6日,正值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的开始,整个国家都处在休息期间;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突然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赎罪日战争”(the Yom Kippur War)正式爆发。几个小时之内,埃及军队就突破了以色列苏伊士运河沿岸的防线,当埃及步兵已经越过以军的坦克阵地时,以色列武装部队理应快速反应以防被袭。在这一波突袭之后,数百辆敌军坦克正向着以色列隆隆驶来。
这是在那场以色列大获全胜的战争—“六日战争”(the Six Day War)之后的第療年;那是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战争,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那场战争之前的1967年,这个刚成立19年的犹太国家,看起来就要在阿拉伯人军队的围攻下解散了。每个边境都有敌人在侵犯,但是,只用了六天的时间,以色列军队就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军队一一击退,扩张了自己的领土,从叙利亚那里取得了戈兰高地,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同时还占领了埃及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
所有这一切让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没人认为阿拉伯国家还会冒险再对以色列发动一次全面进攻。即便是在军队,防御的意识也只是:如果阿?伯人胆敢再次进攻,那么以色列将再次迅速将其击败,就像1967年的六日战争那样。
所以在1973年10月的这一天,以色列并没有作好战斗的准备。面对跨越苏伊士运河浩浩荡荡而来的埃及军队,以色列的防御工事简直不堪一击。在被摧毁的前线之后,有以色列的三个坦克旅,他们位于前进的埃及军队和以色列的中心地带之间,但是只有一个旅的位置与前线临近。
这个旅由陆军上校阿姆农·雷瑟夫(Amnon Reshef)率领,仅配备了56辆坦克,负责保卫长度为200公里的前线的安全。在雷瑟夫和自己的将士一起反击埃及的进攻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坦克接连受到攻击,可是并未看到敌方军队的坦克或者反坦克炮。究竟是什么武器在攻击他们呢?
起初,雷瑟夫认为他们是受到了RPG火箭筒的攻击,这是一种常见的手提式反坦克武器,在步兵中广泛使用。于是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向后撤退一段距离,根据培训,为躲避RPG火箭筒攻击,只要撤退到其短射程之外即可。但是以色列军队的坦克依然陆续遭到攻击,以色列人开始意识到袭击他们的是另外一种武器—一种似乎是看不见的武器。
随着战争的白热化,线索出现了。几名从导弹的袭击中幸存的坦克驾驶员报告说,受到袭击时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但是他们旁边的战士说看到有一束红光射向目标坦克。后来以色列军队在地上发现了电线,这根电线指向被攻击的以色列坦克。指挥官们终于发现了埃及军队的秘密武器:赛格反坦克导弹。
赛格的设计者是Sergei Pavlovich Nepobedimyi,他名字中最后一个词在俄语里的字面意思是“不可战胜的”。赛格诞生于1960年,这种新式的武器最初是专门提供给《华沙条约》成员国的,但是其第一次在战争中投入使用却是在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使用了这种武器。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称,赛格在这场战争中摧毁了近800辆以军的坦克,其中包括在战争开始的第一?,摧毁了拥有100辆坦克的以军第252坦克分队。
赛格是一种线导导弹,只要一个战士躺在地上就可射击。它的射程达3 000米(1.86英里),是普通RPG火箭筒的10倍;另外,赛格的威力也十分强大。
每个射手都可以独立工作,甚至都不需要有人来做掩护—有一个浅沙坑让射手藏身就行。射手只需要将导弹对准坦克的方向,然后在导弹的后面用操纵杆控制红线射击即可。只要负责射击的战士能看到连接着导弹的红线,他就能准确地控制导弹击中远距离外的目标。
其实在这场战争之前,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就已经知道了赛格,甚至在和埃及从1967年战争之后不久就开始的边境消耗战中还遭遇过这种武器。但是以军高级官员认为赛格仅仅是另一种反坦克武器而已,和他们在1967年战争中打败的敌方武器没什么本质区别。因此,在他们看来,敌人的新式武器确实存在,但也无须专门准备以应对赛格的威胁。
在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雷瑟夫和他的战友们必须找出究竟是什么武器在打击他们,同时还要找出应对这种武器的办法。
在彼此交换了看法之后,雷瑟夫及其将士们发现赛格也有其缺陷:它们飞行速度较慢,而且最终是否击中目标依赖于射手盯着以色列坦克的那只眼睛。于是,以色列军队找到了一个新办法:只要任何一辆坦克发现一条红线,所有坦克都开始四处移动,同时对着那个看不见的射手的方向进行射击。
坦克移动扬起的尘土模糊了敌方射手的视线,使其看不清导弹后面的红线,同时以方军队回射的火力也使得射手不得不转移自己的目光。
事实证明,这种新发明非常奏效,后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都采纳了这种方法。这既不是在军事学院的演练中长年形成的教条,也没出现在偶发事件的手册中,而只是战士们在前线的随机应变。
通常,以色列军队的战术创新都是由下而上进行的—由个体的坦克指挥官或者他们的军官向上传递。对于这些战士来说,大概永远不可能发生他们去问自己的上级该如何解决问题,或者说他们没权利决定这么做的情况。当然,对于实时担当起发明、采纳以及传播新的战术之类的任务,他们也不会觉得奇怪。
但是这些士兵的所作所为的确很奇怪。如果他们在跨国公司工作过或在其他军队服过役,很可能就不会做这种事,至少不会自己去做这种事。曾经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担任过联络员的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Michael Oren)说:“以色列军队里的副官,很可能是全世界所有军队里指挥决策权范围最大的军官。”
这种指挥决策权的范围,在我们前面一章讲到过的公司文化里非常明显。在以色列军队里,这种范围即使不比在公司大,至少也会相当。一般说来,当人们想到军队文化时,总是会和严格的等级、对上级绝对的服从联系在一起,每个士兵都只是大轮子里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但是,以色列国防军不在这种军队之列。而且,在以色列,几乎每个人都要在军队服兵役;在两到三年的服役期间,这种文化已经深深地植入以色列公民的灵魂了。
以色列国防军的向下授权是必然之举,也是独创之举。《五角大楼与战争的艺术》(The Pentagon and the Art of War)的作者,《以色列军队》(The Isreali Army)的作者之一,军事历史学家和战略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曾经说过:“所有军队都赞成随机应变的战术:纵观中国、法国或者英国的军队—无一例外都在谈论随机应变的战术。但是,文字本身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你必须从结构上进行观察。”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勒特韦克开始统计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军队人员结构,最后参与统计的一个国家是以色列,该国军队金字塔最上面一层非常窄。勒特韦克说:“以色列国防军特意让高级军官的人数非常少。这是精心设计的结构,这种结构意味着有更少的人发号施令,同时更少的高级官员也意味着底层士兵有更多的主动权。”
勒特韦克指出,以色列军队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陆军上校,而副官或者助理人员的数量却很多。美国军队中高级军官占整个作战部队的比例为1∶5,而这个比例在以色列国防军中仅为1∶9。以色列空军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整体来看,以色列空军的规模要大于法国和英国的空军规模,但是它的高级军官人数却比后两者都要少。以色列空军的最高长官是一个两星级上将,一般来说这个级别要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军队同等位置的军官的级别要低得多。
按照美国的情况,设置更多的高级军官或许是相当必要的;毕竟,美国军队非常庞大,甚至要到远离国土8 000多英里的地方去作战,要在几个大洲之间部署兵力,所面对的物流和指挥方面的挑战是巨大的。
但是,先不论每个军队的规模和结构对于它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来说是否合适,事实上,以色列国防军高层人员较少的人员安排的确在作战中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这种安排带来的好处吉拉德·法希(Gilad Farhi)告诉了我们。吉拉德·法希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少校,已届而立之年。他的职业生涯应该说非常典型:18岁成为突击队的一名战士,然后指挥一个步兵排,之后是连,而后是南方司令部的发言人,后来他荣升为步兵营副指挥,现在他是以色列国防军最近新成立的某个兵团一个即将成立的班的指挥官。
我们是在约旦河谷一个贫瘠的边境基地上见到吉拉德·法希的。当他迈着大步向我们走过来时,无论是那年轻的面庞还是他的衣着(皱巴巴的标准步兵制服)都不会让人想到,这是一位基地的指挥官。在他的新兵到来之前,我们采访了他。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法希要负责650名新战士的基础训练工作,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刚刚高中毕业,另外还有120名军官、小队指挥官、军士以及行政管理人员。
法希告诉我们说:“?这里,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些连队指挥官,他们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这是一群孩子,年龄大都在23岁左右,每个人手下有100个士兵、20个军官和小队长、3辆车。把这些加起来就意味着120支步枪、机关枪,和炸弹、手榴弹、地雷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真是责任重大啊!”
连队指挥官也是需要为所属领域负责的最底层的官员。法希说:“如果有恐怖分子侵入某连队所属的领域,那么该连队指挥官的名字将和这件事息?相关。请问,在这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有哪些23岁的年轻人能承担得了这种压力?”
法希通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向我们诠释了这些23岁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执行的一次任务中,法希的一个连队有一名受伤的战士被恐怖分子围困在一栋房子里。此时,连队指挥官只有三样东西可供调配使用:一只攻击犬,他的战士,还有一台推土机。
如果这名连队指挥官放出攻击犬,那么它有可能会去攻击受伤的战士而不是恐怖分子;如果他让推土机去破坏房子,那也很有可能会伤到这名受伤的战士;如果他派兵闯入房子,?要面临造成更大伤亡的风险。
更复杂的是,这间房子的隔壁就是一所巴勒斯坦学校,孩子们正在里面上课。在学校的房顶上,记者们正在记录整个场面,同时恐怖分子也正在朝着以色列军队和记者的方向进行射击。
“这个时候,这名连队指挥官所面临的麻烦数都数不清,而且你不可能指望能从书本中找到解决的办法。面对这种复杂的状况,指挥官回到基地,他的战士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看着他,他自己也感到有所不同。他正在前线—要为那么多人的生命负责:他的战士、巴勒斯坦学生、记者。看看,他不能征服整个东欧,可他必须想到一个办法来?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而他才仅仅23岁。”
后来我们还听说了约西·克莱因(Yossi Klein)—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一个20岁的直升机驾驶员的故事。当时,他奉命深入黎巴嫩南部解救一位受伤的战士。当他驾驶飞机到达战场之后,他发现那名受伤的士兵躺在担架上,周围遍布浓密的灌木丛,他的飞机无法正常着陆,即使悬空也无法充分接近地面,以便把担架移到飞机甲板上。
没有课本告诉克莱因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即便有,它们也不会建议克莱因使用他发明的这种方法:用飞机的尾部螺旋桨,看起来有点像割草机,砍倒周围的植物。他这么做,意味着在任何时候,螺旋桨都随时可能坏掉,然后带着他冲向地面。但是,克莱因成功地把灌木丛削低了,这样他就可以盘旋在空中,充分接近地面,把战士接到飞机上去。然后他载着这名战士奔向以色列的医院,最终这名受伤的战士得救了。“有多少和克莱因一样的同龄人会在他们上大学的时候经历这种考验呢?你会用这种方式去培养和锻炼一个20岁的年轻人吗?”法希问我们。
在以色列军队,当局放权给底层的力度之大常常让人惊讶,甚至连以色列的领导人有时也会为此大吃一惊。1974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第一届任期期间,以?列国防军的情报部门8200—Fraud Sciences的创立者曾服务于这个部门—有一名年轻的女战士被恐怖分子绑架了。以色列的这个部门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阿哈伦·法卡什(Aharon Farkash)是该部门的最高长官。他回忆起当时拉宾的疑虑:“被绑架的女孩是一名军士,拉宾让我们提供一份详单,逐条列出这个女孩所知道的所有事项,他担心一些机密的信息会从这个女孩嘴里泄露出去。拉宾看到那份清单后,焦急地告诉我们需要立即展开一次调查:一个普通的军士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对于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的机密信息呢!这究?是怎么回事?”
法卡什继续为我们讲述这件事。他说,当拉宾在六日战争期间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统帅之时,这种情况让他更加惊讶。“我告诉他说:‘总理先生,这个军士并不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么多机密信息的军士。这不是个错误。在8200,所有战士都必须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向他们隐瞒这些信息,我们就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完成工作—我们没有足够的军官来做这些。’事实上,人为地对信息加以限制,去建造另一种体制,对我们来说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个系统一直没有改变。”
法卡什现在经营一家公司,为企业和居民设施提供创新?安全系统。他诙谐地说,这可谓是最强大的力量,以色列缺少四个“总”—总领土、总人力、总时间、总预算。“但是如果缺少总人力的话,就什么事也干不了。我们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配置那么多的军官,所以我们的军士做的其实就是陆军中校的工作。确实如此。”
人力资源的匮乏同时还是另外一个现象的原因所在,那就是预备役部队在军队中的作用。这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以色列国防军最具特色之处了。与其他国家不同,预备役部队是以色列军队的支柱。
大部分军队的预备役部队只是常备军的附属物,常备军才是国家安全防卫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以色列一个这么小的国家,面对数量远远超出自己的敌人,从一开始他们就很明白,他们的常备军是不可能强大到能对付如此大规模的袭击的。独立战争之后不久,以色列的领导人就决定构建一种独特的军队结构,预备役军人不仅单独编制,全员都是预备军人,而且指挥官也由预备军人来担当。在其他国家,预备役部队一般是由常备军的军官来指挥的,而且在正式投入战争之前,至少也会有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新兵训练。“没有哪个部队依靠的主力是一群刚刚招募来两天甚至一天就投入战争的战士。”勒特韦克说。
没有人确切知道以色列独特的预备役制度是否会奏效,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这么做。甚至到了今天,以色列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这?制度的国家,正如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所说:“用这种方法管理军队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但是以色列人做得很好,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以色列的预备役制度不仅仅是这个国家创新的一个例证,同时,它还是国家创新的催化剂。当一个出租车司机能指挥百万富翁、23岁的年轻人训练自己的叔叔时,等级制度自然就消失了。预备役制度从本质上强化了这一点,反等级的理念在以色列社会随处可见,从作战室到教室,再到董事会会议室,它无处不在。
纳提·罗(Nati Ron)在生活中是一名律师;在预备役部队中,他是一名陆军少校,指挥一个团?。“等级在预备役部队中根本就不存在,”他告诉我们,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一件事,“一个普通士兵可以在训练中告诉一名将军:‘你这么做是错误的,应该那样做。’”
阿莫斯·戈伦(Amos Goren)是特拉维夫市安佰深公司的一名风险投资家,他非常同意上述观点。阿莫斯曾经全职服务于以色列突击队5年之久,之后的25年他一直在预备役部队。“在这30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向任何人行过致敬礼。我甚至不是一名军官,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勒特韦克说,在预备役制度形成之时,完全平民化的氛围就渗透到了军队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这并不是说战士们就不用服从命令。戈伦解释说:“以色列士兵的区别不在于军衔等级,而在于其所擅长的领域。”或者,如勒特韦克所说:“发布命令和服从本身只是意味着某人有一项工作要做,而且做好很重要。等级的影响很小,尤其是当所谓的等级常常穿梭在年龄和社会地位上差别很悬殊的人之间时。”
当我们问少将法卡什,为什么以色列的军队能做到如此不受等级的约束,而且可以公开质疑和讨论任何事情呢?他告诉我们不仅部队如此,以色列整个社会和历史亦是如此。“我们的宗教本身就是一本开放的书。”法卡什说,带着些微的欧洲口音,这要归因于他早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经历。法卡什所说的“开放的书”是指《塔木德》—几百年以来拉比们之间关于犹太律法的公开讨论的集大成之作—这种精神不仅影响了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也塑造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
正如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所说,犹太教和以色列人始终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从犹太文明开始存在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
以色列国防军中无等级之分的做法渗透并现实地影响着普通人的生?,这种影响甚至会打破普通民众中的等级概念。“教授会尊重自己的学生,老板会敬重自己的高级文员……每个以色列人都有几个来自‘预备役’的朋友,他们或许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中不会有任何联系,但他们曾经一同睡在露天的木屋或者帐篷里,一起吃过无味的军队食物,常常几天不洗澡,一群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平等地聚在一起。以色列还是阶级差异最小的国家,在这方面预备役制度功不可没。”勒特韦克说。
众所周知,在其他国家,对等级和地位如此淡漠的情况并不多见。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军官兼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发生在?色列军事基地的典型场景,当时他在部队从事联络工作。“你和一大群以色列将军围坐在一起,然后大家都想来一杯咖啡,那么离咖啡壶最近的那个人就会去为大家准备咖啡。无论这个人是谁,实际上是谁并不重要—对于那些将军来说,为他们的士兵准备咖啡是很平常的事。当然,士兵为将军准备咖啡也是非常平常的事。没有人规定这些事。但是,如果你是和美军的队长在一起,这时一位陆军少校走进来,每个人都会立刻紧张起来;然后,陆军上校进来了,陆军少校也会立刻紧张起来。在美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大家在美国军队看到的那样?‘你是在向地位致敬,而不是在向军人致敬’。”
在以色列国防军里,甚至还存在一些极端不合常规的制度支持人们对高级军官发出挑衅。奥伦告诉我们说:“我所在的以色列部队,可以直接否决自己的军官,人们只要聚在一起,然后投票决定即可。我亲眼目睹过两次这样的事情。我真的非常喜欢那个人,但是我投了否决票,我们选出了另外一个上校。”当我们惊讶地问奥伦这是怎么回事时,他解释说:“你走过去然后说:‘我们不想让你领导我们了,你不够优秀。’我的意思是,大家关系都很好……你走到级别比你高的那个人面前说这些,那个人会离开?…在这里,一切都是以你的表现为导向的,而不是以你的地位。”
退休的国防军将军“妖怪”摩西·亚阿隆曾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担任军队总参谋长,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事情发生在第二次?巴嫩战争期间。“当时在黎巴嫩的达布村有一场预备役部队参加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有9名士兵和军官牺牲了,还有很多人身受重伤,其中就有我的侄子。后来,活着的战士认为,本场战斗的营长指挥不力才导致了如此惨重的伤亡,于是他们到了旅长那里,指责营长在战斗中不合格的表现。然后旅长就此事展开了调查,因为部下们所发起的一次抗议活动后来那个营长被迫下台了。”
亚阿隆相信以色列军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也正是其效能发挥的关键所在:“对于领导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士兵对他的信心。如果你不相信他,如果你对他没有信心,你就?可能跟随他。如此说来,那个营长的确是失败的。或许是专业能力方面的失败,就如这个例子一样;或许是道德方面的失败,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无论怎样,战士必须确信领导是被认同的—有号召力的—号召他主动参与各种事务。”
前西点军校教授弗雷德·卡根(Fred Kagan)认为,美国可以从以色列方面借鉴一些经验。他说:“我并不认为一个指挥官总是担心自己的下属会不会越级去揭发自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就像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里的做法一样。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在美国军队里,一个军官想要获得晋升,晋升委员会如实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评?,这会给军队带来诸多好处。问题是现在在我们的体制中,激励都只来自于一方面,为了获得晋升,一名军官必须取悦越来越多的高级军官,底层的军官什么益处也得不到。”
奥伦从绝大部分军队中总结出来的结论(弗雷德·卡根称之为“不服从”)是:事实上,以色列国防军“比美国军队要和谐、主动得多”。这个结论看起来很奇怪,因为美国的军队号称是“志愿”军(虽然无偿,但有自由选择感),而以色列国防军是靠征召才建立起来的。
但是,奥伦解释说:“在这个国家有一个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我们服务于这个政府设立的军队,军队会为?们负责……我想,比起2008年的美国军队,以色列军队的情况与1776年的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更为相似……顺便提一下,乔治·华盛顿就很清楚他的‘将军’地位并不代表什么;他必须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从根本上说,那就是要让人们发自内心地跟随他。”
奥伦所说的大陆军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这里的战士几乎每天都可以决定要不要继续做个志愿者。但是它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以色列国防军也是。正如奥伦所说,他们过去或者现在拼凑在一起,不正规但是很默契;因为他们过去或者现在是在为自己国家的存亡而战,由各个领域的人组成?为彼此而战。
不难想象,如果一个士兵不用因为告诉他的老板“你是错的”而忐忑不安,那他自然也就不会顾忌地位的问题。这种“肆无忌惮”,再经过在国防军里服役几年的锻炼,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施瓦特·沙克德能在贝宝的总裁面前高谈网络上“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你也会理解英特尔的以色列工程师们如何敢执著地煽动公司管理层改变最基本的原则,放弃最核心的产品,选择更有行业价值的产品。自信与傲慢,挑剔、独立思考与不服从,雄心勃勃、远见卓识与莽撞自大—根据你自己的看法随便用哪个词吧,但是这就是典型的以色列企业家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