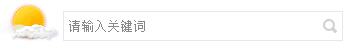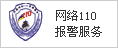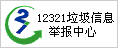中国城市近年来硬件设施发展迅猛,各种金融区、高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整体成果。但另一方面,北上广大城市交通拥堵,雾霾污染始终挥之不去,困扰着居民。北京最近就出台了建立“副中心”的规划消息,针对这个规划思路,本网记者近日在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治理和发展国际论坛上,专访了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博士。刘博士说建立“副中心”需要先进行系统研究规划,并对“副中心”的规划进行标准量化,把北京主体内部的人口和功能进行卫星城式的分区块调整后,再逐渐迁移。同时他也谈到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规划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思路,指出中国应该保留好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
整体规划的关键在于划分标准区域 人口和设施边匹配边扩迁“副中心”
记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合理规划已经成为大中小城市的重要工作。以北京的城市规划为例,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医疗、旅游等方面的优势功能和资源几乎都在北京聚集,这可能是造成人口数量过多的原因之一。对于功能资源和人口过于拥挤的状况,北京正在研究采取减负规划,例如建立“副中心”,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太格:这当然是可行的。但是不希望只强调解决人口多的问题,而是先要将城市治理得健康均衡,再把人口合理有序地分流出去,合理配套设施,这样分流出去的部分也是健康的。城内城外都是健康的,所以不要把城内和城外的关系分得太绝对。
对于“副中心”,首先,我觉得谈规划要把所有的名词来做一个量化定义。什么叫副中心呢?规模有多大,里面的建筑面积是多少?服务人口是多少?服务的半径是多少?这些概念都需要明确。现在有很多新鲜的名词,这些名词都是什么意思要先搞清楚,这也是当前规划界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在说一些新鲜的名词,但它们到底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如果定义还没清晰就进行规划,很容易天下大乱。
中国的城市规划需要静下心来,分析城市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然后根据需要,和专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新加坡独立不久,那时候也是完全没有经验的,所以新加坡政府就找联合国城市规划署在1968年到72年间为新加坡做一个概念式规划,当时的规划成为今天的新加坡基本雏形,而且政府很注重这个方案的延续性。幸运的是,1972年的概念式规划到今天来看,还是非常合理的。
记者:先均衡调整人口和基础设施的比例,再迁出。就像医学抽脂减肥一样,如果不调整身体和饮食,接下来还是解决不了肥胖。现在北京作为首都,面临着外地来京的人口压力非常大,您有何规划建议?
刘太格:这个关于本地外地的人口压力划分我觉得还是很片面的。比如说,一个大城市切成若干个中等卫星城市,每个中等城市都有自己的配套设施。那么到底外地人到哪里去满足自身的需要,就需要根据哪个区块城市的设施比较好来定。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外地人,北京本身2000多万人口,本地人的需求就不得了了。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可以把中心打散,学校、医院,甚至文化中心均衡设立。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有中心医院,每个片区都有它的医院,每个医院有它特殊的技术能力,换言之也是一个区域性的医疗中心。有很多人从俄罗斯甚至中东到新加坡治疗,因为我们的医疗技术很好。但病人并不一定都需要到中心医院,他可以根据区域医院的不同特色,进行选择。
具体来说,首先应该先把大城市切成六七个健康的卫星城市,然后再把人口和功能部门往外划分,否则单纯迁人口和功能部门都是搞不好的。因为任何城市都需要人口支撑,而人口需要合理的基础配备,这样才可持续。所以我今天也强调,首先第一件事要敲定人口。不是说今天把大城市多出来的300万人口直接搬进新的微型城市,而是先将微型城市现有的人口和基础设施调整匹配,例如人口有三十万,你先给三十万做好基础配套服务,那么做得好的话,人口就可以增加到六十万了,那么再做配套,再迁移,逐步推进北京减负,同时也对新城市有一个合理的城市规划。
这样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家庭,有大小不等的成员。每个卫星城市可容纳两三百万人口。而每一个卫星城市都需要进行配套建设,包括中央商务区、大学等等。那么在朝阳区的民众就不需要整天跑到海淀区去办公和学习了。因为他生活上的需要在他本身居住的区域就已经得到满足了。这样做首先可以解决交通问题,其次会把北京变成一个低碳的城市,最后将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总的来说,我认为解决内部的问题就是解决外来的问题。先对城市进行一个系统化的规划,而不是建立副中心。没有系统化的规划,我们并不能认为北京的副中心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记者:您的意思是,先以划分区块为基础,然后再向外扩展。先解决内部问题,再设置副中心。
刘太格:其实跟家庭一样,要整体化规划,最关键是先把人口分摊好。北京目前的塞车以及雾霾问题就是由于城市系统问题,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副中心长期的作用可能也是不大的。其实我也是医生,不过我的病人是城市。这句话是有含义的。中医跟西医差别在哪里?西医是治标不治本,中医是治本,治本病就会好了。规划要治本,现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就是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
记者:刚才您说了北京这样超大城市建立副中心的看法,那么对于目前中国整体的城市规划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刘太格:首先,城市规划要做得好,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项目工程。如果没有系统的规划,只关注项目工程,是无法解决交通、基础设施这些系统化问题的。而且,交通跟城市规划是分不开的。但如果你只是考虑交通,把路布了,而没有考虑怎样把这个交通带到商业上,这个系统就不完备了。政府、企业在实施方案的时候,需要自己全面了解方案。城市的功能要完善,尤其是商业中心要匹配。
其次,政府应尽可能地完成项目,方案出来之后,必须要尊重这个方案,而且要有一定的延续性。城市规划是严肃且高度系统化的工程,我觉得这一点很多地方政府认识不够,总是以为城市建设就是项目,从国外引进先进理念后,没有正确应用这些理念,这本身需要从系统角度来考虑。当然有人会说有时间限制,希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把系统工程做好。其实在总体规划系统工程的那一年,其他工程项目照样可以推动。可是,当系统方案完成以后,地方领导一定要了解这个方案的原则在哪里,要重视这个方案,而且今后的工程要根据这个方案来,这个决心我觉得还不是很明显。
城市建立标准化模型便于政策实施 同时应保留好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
记者:从中央政府的思路看来,保障性住房和城镇化是两项重要工作。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和保障房的发展状况?
刘太格:目前中国有关公共住宅的政策太多了。保障房、廉租房、拆迁房等等,这样的话,相关负责机构就很多。新加坡为什么公共住宅做得好,就是因为新加坡只有一个公共住宅政策。所以你在一个卫星镇里面,人均收入多样化,把居民都放在一起,这个社区就变成综合性的。里面的配套是供大家用的,所以就比较齐全。而且,在这样的社区里面,需要服务的人也是高低不等,各个阶层都有。目前,中国领导很希望解决住房问题,可是现行政策本身有很多障碍。
当然有人问,中国那么大,怎么可能有同样的政策。其实完全可以把政策分到省里面,省再分到市里面,每个市的规模就差不多相当于新加坡了,然后再让他们去处理公共住宅问题。新加坡过去是有农民的,但现在都没有了,因为在新加坡,市民和农民住在一起,在15、6年之内就实现城市化了。城镇化需要一个具体的政策,要中央从省一级一步一步分下去,城市的问题还是要由每个城市来解决。
记者:您提到新加坡过去也存在农民城镇化的进程,那么中国几亿农民的城镇化过程中,您认为政府规划应该注意哪些地方?
刘太格:中国一定会走发达国家的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在80%到90%,现在中国是50%多,所以中国的一线城市,不应只为目前的人口来规划,应多预留空间给未来的外来人口。不过,与此同时,应保留一些城镇。比方说中国未来城市化率能达到75%,那么我认为其中10%应留在镇里面。因为中国历史这么丰富,很多好东西都在大小城镇里面,不要把它破坏掉。
我祖父的老家在福建,最近在看老照片,真是美得不得了!我不希望中国的城市都变成超大城市。我觉得这个“镇”的概念提得很好,就是说我们除了解决城市的问题,也应该把中小城镇尽量保护好。因为中国跟欧洲一样,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很多中小型城镇,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只要解决好城镇的基础设施、交通等问题,选择若干个有特色的城镇进行保护,中国的小城镇有潜力发展为欧洲那种精致的古镇。
另外,规划最后是要搞硬件,可是硬件的背后,需要软件思维。要考虑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交通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在考虑硬件规划的时候,还要考虑硬件规划出来以后会给软件带来什么影响。这个是中国城市规划需要注意的问题。
记者:我们还有一个担忧是城镇化成功后,将会多出大量不再务农的农民,他们将依赖什么资源生存发展?
刘太格:中国的老镇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一定的文化价值。地方有地方艺术,比如说有盆雕艺术、老建筑等等,这种旅游资源能转化成经济来源。把农业做成工业化,这个可能性也相当多。所以不要拿问题来当借口,把这个问题推掉。
讨论的目的在于找答案。很多人来学习新加坡经验之后认为两国国情不一样,难以实现。我认为基本的原则是到各地都可以实行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来克服行政上的障碍,把它做好,有没有理解新加坡经验的内涵优势。所以我们要把重点从问问题转移到找答案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